疫情期间的场景描写(疫情期间的场景描写片段)
2020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,街道两旁的樱花开了又谢,却少有人驻足,这座曾经喧嚣的城市,如今只剩下红绿灯机械地变换颜色,仿佛时间的流逝在此刻变得格外清晰。
我站在阳台上,望着楼下空荡荡的街道,偶尔有一两个行人匆匆走过,戴着口罩,低着头,步伐比平时快了许多,他们的身影在阳光下拖出长长的影子,却又很快消失在拐角处,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,混合着初春的微凉,让人不自觉地紧了紧衣领。
小区的门口搭起了临时帐篷,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志愿者手持体温枪,为每一个进出的人测量体温,他们的面罩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,看不清表情,只有疲惫的嗓音从口罩后传来:“36度5,可以进了。”居民们默契地排成一列,彼此间隔一米,没有人说话,只有鞋底摩擦地面的沙沙声。
超市的货架上,泡面和速冻食品总是最先被抢空,收银台前,人们推着购物车,眼神警惕地扫视四周,仿佛空气中漂浮着无形的威胁,收银员戴着橡胶手套,动作麻利地扫码、装袋,偶尔抬头看一眼顾客,又迅速低下头去,塑料帘子被掀开时发出“哗啦”一声,像是打破寂静的唯一声响。

地铁车厢里,座位被贴上了“间隔就坐”的黄色标签,乘客们像棋盘上的棋子,整齐而疏离地分布着,有人低头刷手机,有人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广告牌发呆,广播里循环播放着“请佩戴口罩”的提示,声音温和却不容置疑,偶尔有人咳嗽一声,周围人的身体便会不自觉地绷紧,目光如探照灯般扫过去,又迅速移开。
医院的发热门诊前,队伍蜿蜒如长蛇,人们裹着厚厚的羽绒服,在寒风中跺着脚取暖,护士们穿梭其间,手中的登记表被风吹得哗哗作响,一位老人坐在轮椅上,膝盖上盖着毛毯,他的女儿站在一旁,不断调整着他的口罩边缘,老人的眼神浑浊,却紧紧盯着医院的大门,仿佛那里是希望的入口。
公园的长椅上落满了灰尘,曾经聚集在这里跳广场舞的大妈、下象棋的老头、追逐打闹的孩子,如今都不见了踪影,只有几只麻雀蹦跳着啄食地上的面包屑,偶尔警惕地抬头,又继续它们的饕餮,远处的健身器材孤零零地立着,铁质的表面在雨中泛着冷光。

学校的操场空无一人,教室的窗户紧闭,黑板上还留着放假前未擦净的粉笔字迹,走廊上的荣誉榜里,照片中的孩子们笑得灿烂,而此刻他们的面孔被口罩遮盖,只能通过眼睛辨认彼此,网课的提示音在千家万户响起,老师们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来,偶尔夹杂着电流的杂音,像是某种遥远的信号。
夜晚的城市依旧灯火通明,却少了往日的烟火气,高楼大厦的霓虹灯倒映在空旷的街道上,像一场无人欣赏的灯光秀,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车飞驰而过,尾箱里装着热腾腾的餐食,却无法装下人们对团聚的渴望,阳台上,有人点燃一支烟,红色的光点在黑暗中明灭,像是沉默的叹息。
疫情改变了城市的脉搏,它让亲密变成距离,让喧嚣变成寂静,也让平凡的日子变得珍贵,当口罩成为生活的必需品,当“健康码”成为通行的密码,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瞬间——一个微笑,一次握手,甚至只是拥挤人群中不经意的擦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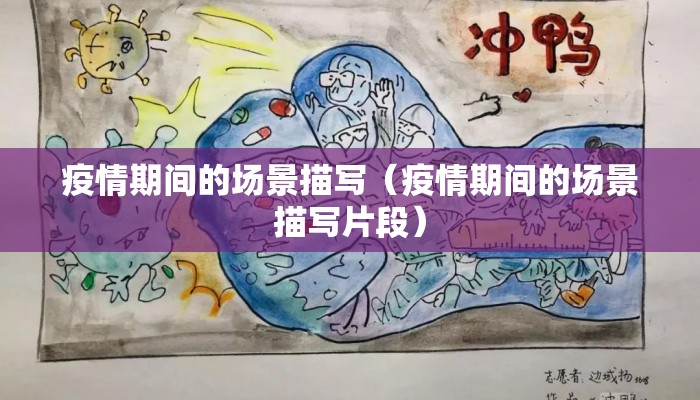
而在某个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,洒在重新热闹起来的早市上,当小贩的吆喝声、豆浆的香气、孩子的笑声再次填满街道时,我们会记得,这片土地曾如何安静地等待重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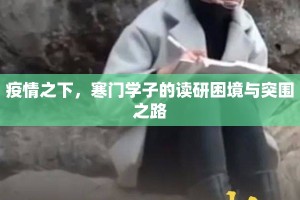


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