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初春的那个早晨,我站在窗前,望着空荡荡的街道,突然意识到世界已经变了,小区门口的喇叭循环播放着防疫通告,超市货架上的方便面被抢购一空,手机里不断弹出令人心惊的疫情数字,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,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,剖开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表皮,暴露出许多被日常忙碌掩盖的真相,在这被迫停摆的三年里,我经历了一场与自我、与他人、与世界的深度对话,那些曾经被忽视的微小事物,突然在隔离的寂静中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回响。
居家隔离的第一周,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,每天刷新疫情数据的手指停不下来,冰箱里的食物要精确计算到克,连窗外飞过的鸟都让我神经紧绷,直到某天深夜,当我第三次检查门锁是否关好时,突然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扭曲的面容——那是一个被恐惧完全占据的陌生人,那一刻,我意识到病毒最可怕的不是攻击肺部,而是吞噬心灵的平静,我开始尝试冥想,在阳台上种起了小葱和薄荷,重新拾起荒废多年的素描本,当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取代了手机通知音,我找回了久违的专注力,疫情像一面放大镜,让我看清了自己情绪调节能力的贫乏,也意外地打开了一扇通往内在世界的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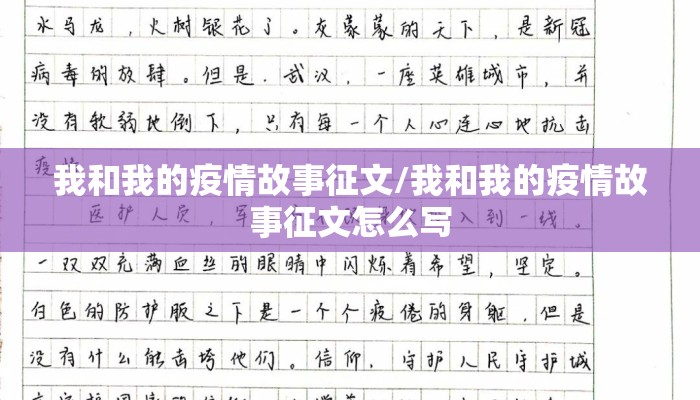
封控期间,我与邻居们的关系发生了奇妙的变化,曾经在同一栋楼住了五年都不知道对门姓什么的都市冷漠,被团购接龙和物资互助彻底打破,记得三楼的老教授把珍藏的茶叶分给每家一小包,七楼的护士姑娘在业主群里分享消毒知识,而我则成了帮整栋楼打印学生作业的"临时文印中心",最难忘的是张阿姨,她独居且腿脚不便,整栋楼轮流给她送饭,解封那天,我们在院子里分享了各家拿手菜,孩子们在草坪上追逐,阳光照在每个人口罩上方的笑眼里,这种被危机唤醒的社区温情,让我重新思考现代社会中"附近"的意义,钢筋水泥的森林里,原来一直存在着守望相助的可能,只是我们习惯了低头赶路,从未抬头看见。
疫情第三年,我养成了记录的习惯,日记本里贴满了核酸检测贴纸,夹着干枯的樱花和梧桐叶,记录着城市从停摆到复苏的每个细微变化,街角那家咖啡馆几次濒临倒闭,最后转型成社区图书交换站;对面的小学操场周末变成露天电影院;我常去的健身房教练开始线上直播课,他的背景里总有一只橘猫慵懒地走过,这些碎片拼凑出一幅韧性生长的城市图景,最触动我的是地铁站里卖唱的盲人歌手老周,当乘客锐减收入断绝后,他学会了直播,摄像头前那把磨损的吉他和永远挺直的背影,教会我什么是真正的"适应力",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,脆弱与坚强原来可以如此并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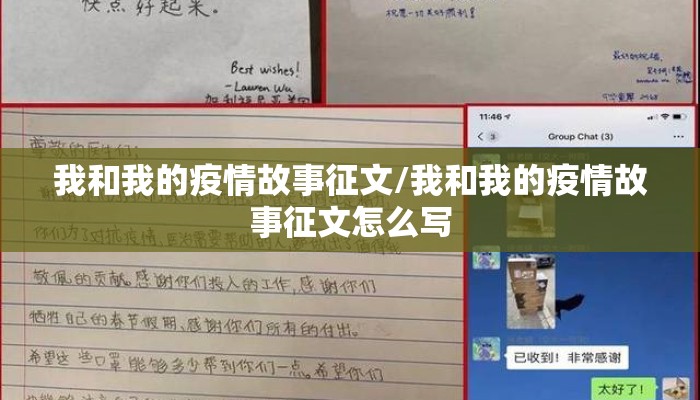
站在疫情后的今天回望,那些囤积的口罩、空荡的街道、窗上的夕阳、群里的接龙,都已成为记忆博物馆里的特殊藏品,这场全球性的暂停,强行打断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,却也提供了难得的反思空间,我学会了在不确定性中保持平衡,重新发现了被忽视的人际联结,见证了平凡生活中的非凡韧性,如果说疫情给世界留下了什么礼物,或许就是这种被迫慢下来后的清醒认知——关于何为必需,何为珍贵,当生活重新步入正轨,我带着这三年的馈赠继续前行:阳台上依然种着薄荷,见到邻居会主动问候,周末偶尔去老周的直播间听他唱《光明》,那些裂缝中透进来的光,永远改变了我看世界的角度。
本文来自作者[杭圣]投稿,不代表小牛号立场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://zyzjtn.com/shhbk/3357.html


评论列表(4条)
我是小牛号的签约作者“杭圣”!
希望本篇文章《我和我的疫情故事征文/我和我的疫情故事征文怎么写》能对你有所帮助!
本站[小牛号]内容主要涵盖:小牛号, 精准资讯, 深度解析, 效率读本, 认知提效, 每日智选, 决策内参, 信息减负, 高价值资讯
本文概览:2020年初春的那个早晨,我站在窗前,望着空荡荡的街道,突然意识到世界已经变了,小区门口的喇叭循环播放着防疫通告,超市货架上的方便面被抢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