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年12月,当"新十条"政策宣布时,许多人并未意识到这竟是三年抗疫马拉松的最后一公里,没有盛大的闭幕式,没有预想中的集体欢呼,只有药店门前排起的长队和社交媒体上不断更新的"阳过"日记,这个被历史选中的最后一个月,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,将我们集体推向了某种终结——不是疫情本身的终结,而是作为一种集体生活方式的"抗疫时代"的终结,当我们站在2023年的门槛回望,那个充满矛盾与困惑的最后三十天,已然成为一段正在被迅速遗忘的集体记忆。
药店的货架上,退烧药和抗原试剂盒成了最抢手的年货,这种突如其来的物资焦虑,与2020年初的口罩荒形成了奇妙的呼应,在最后一个月里,人们重新体验了三年前的那种不确定感——只是这次,主角从"会不会感染"变成了"什么时候感染",社交媒体上,"阳过"成为某种身份标识,朋友圈里晒出的两道杠照片取代了往日的核酸检测记录,这种集体行为背后,是一种微妙的心理转变:从恐惧病毒到接受病毒,从被动防疫到主动迎接感染,在北京某三甲医院,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呼吸科医生告诉我:"12月中旬那两周,我们接诊量是平时的五倍,但奇怪的是,焦虑的病人少了,认命的多了。"这种集体心态的变化,或许正是三年抗疫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烙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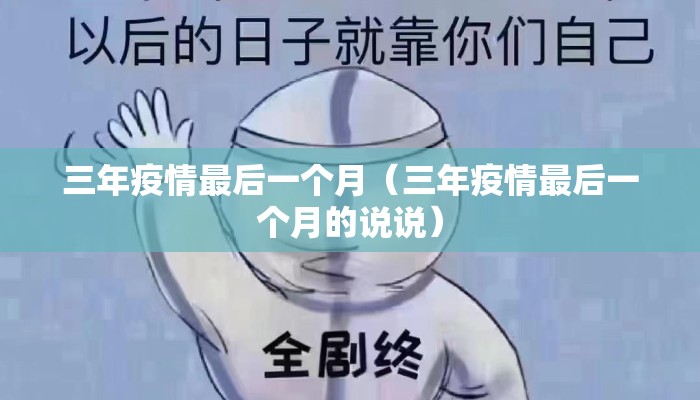
疫情最后一个月最吊诡之处在于,它同时是结束也是开始,当专家们争论"群体免疫"是否已经形成时,普通百姓正在用身体投票——通过实际感染来终结这场持久战,在上海静安区的一家咖啡馆里,我遇到了28岁的平面设计师小林,她在12月20日确诊阳性,却将此视为"赶上了末班车"。"我们办公室15个人,到圣诞节那天只剩下2个还没阳的,他们反而成了异类。"小林笑着说,眼神里却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落寞,这种将疾病经历转化为社交资本的微妙心理,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:我们太渴望某种确定性了,哪怕是"必阳"这样的负面确定性。
教育系统在这个最后一个月里展现了惊人的韧性,某重点中学的教务主任王老师向我展示了他的手机相册:12月5日,教室里坐满了戴着N95口罩的学生;12月12日,一半座位空着;到了12月19日,教室里只剩下零星几个学生,其他人都转入了线上教学。"最困难的时候,我们一个年级12个班主任,倒下了9个。"王老师说这话时,语气平静得令人心碎,而到了1月初新学期开始,一切又神奇地恢复了正常,仿佛那个混乱的12月从未存在过,这种集体遗忘的速度,或许是人类心理的自我保护机制,却也让我们失去了从这场世纪疫情中汲取教训的机会。

在最后一个月里,最容易被忽视的是那些始终处于边缘的群体,外卖骑手老张告诉我,12月是他三年来最忙的一个月。"以前是送餐,现在是送药,以前怕传染给别人,现在是别人怕传染给我。"这位45岁的河南汉子苦笑着展示他手机里一天18小时的接单记录,而在城市的另一端,独居老人李奶奶的抽屉里整齐地码放着社区志愿者送来的退烧药,每盒药上都细心地贴着服用说明。"孩子们说要回来照顾我,我让他们别回来,万一路上感染了呢?"82岁的李奶奶说这话时,眼神飘向窗外空荡荡的街道,这些普通人的微小叙事,构成了宏大历史最真实的注脚。
站在后疫情时代的开端回望,那个充满矛盾的最后一个月,实际上是我们集体心理的一个缩影,三年来积累的防疫知识、养成的卫生习惯、形成的社交距离,在一个月内被全盘推翻,这种认知颠覆带来的不适感,远比病毒本身更令人困扰,正如社会学家项飙所言:"疫情没有教会我们什么,它只是放大了已有的问题。"当北京某三甲医院的门诊量在2023年1月突然回落到正常水平时,我们才惊觉:原来结束可以如此突然,又如此平淡。

三年抗疫的最后一个月,没有鲜花也没有掌声,只有无数个体默默承受的身体痛苦和心理调适,这段正在被迅速遗忘的记忆,或许会在某个未来的冬天突然苏醒,提醒我们曾经共同经历过什么,而眼下,最好的纪念方式,可能就是承认我们尚未真正理解这一切的意义——那个最后月,既是一个时代的终结,也是另一个时代尚未完成的开始。
本文来自作者[珀绎]投稿,不代表小牛号立场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://zyzjtn.com/bkdq/299.html


评论列表(4条)
我是小牛号的签约作者“珀绎”!
希望本篇文章《三年疫情最后一个月(三年疫情最后一个月的说说)》能对你有所帮助!
本站[小牛号]内容主要涵盖:小牛号, 精准资讯, 深度解析, 效率读本, 认知提效, 每日智选, 决策内参, 信息减负, 高价值资讯
本文概览:2022年12月,当"新十条"政策宣布时,许多人并未意识到这竟是三年抗疫马拉松的最后一公里,没有盛大的闭幕式,没有预想中的集体欢呼,只有...